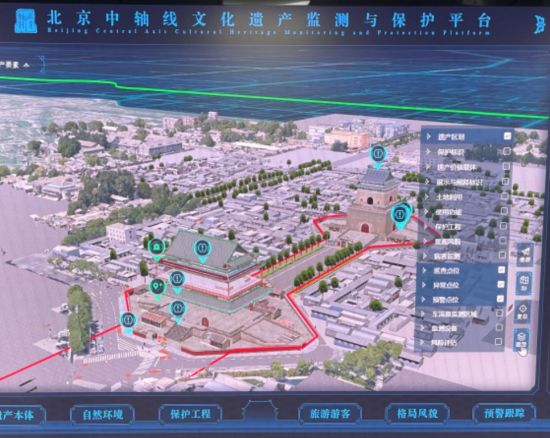
围绕宗庆后的遗产争夺案,正出现新的变数。根据“正在新闻”报道,杭州已成立专班介入,希望能尽快能处理这个事情。
当很多人围绕豪门恩怨在吃瓜的同时,却忽略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。那就是这场本属“家务事”的内部争夺,不能危及娃哈哈的品牌价值。毕竟娃哈哈的大股东是杭州市上城区国资委,不是宗家。
但现实的剧本却以惊人的速度滑向了另一条轨道,随着家族信托、隐秘子女身世等越来越多的剧情被披露,大众对娃娃品牌的印象,正变成“家族斗法”的代名词,甚至把娃哈哈调侃为“娃多多”。
公众信任感的流失,正在击穿这家企业几十年积累的声誉资产,这对娃哈哈而言,远比二股东的股权归属更危险。专班的设立,显然不止于处理家事,更关键的是不要让日渐脱轨的剧情,把曾经的国民品牌拖入豪门内斗的漩涡。
一切风暴的起点,始于失控。宗庆后建立的那个以他个人为核心的治理体系,在他离去后,迅速暴露出了其脆弱性。
从目前透露出的各种剧情来看,其烈度远超外界想象。这并非一场围绕战略方向或经营理念的商业分歧,而是一场赤裸裸的、几乎不加掩饰的权力争夺。舆论场上,各种爆料迭出,将家族内部的矛盾公之于众。
而在水面之下,为争夺控制权所进行的一些商业运作,恐怕更加釜底抽薪。据目前透露出的信息来看,双方为争夺控制权,都先后在娃哈哈外设立各种循环体系,本质上是把集团的利益转移到自己控制的体系里。
如果仅仅是家族企业,还可以理解成继承权博弈。但当行动方仅仅是二股东,且大股东为国资的时候,这就是一种危险的游戏,甚至可以看作是,以牺牲企业根本利益为代价的资产腾挪和控制权掏空。
当企业的核心管理层不是聚焦于市场竞争、产品创新,而是将大部分精力转向内部的权力角逐和利益分割时,这家企业就已经站在了悬崖边缘。
某种程度上而言,这场源于家族内部的争夺,已经对品牌资产造成无情的侵蚀。娃哈哈的核心资产,不仅是遍布全国的厂房、生产线和深入毛细血管的渠道。更是其在几代消费者心中,沉淀下来的、关于“国民饮料”的集体记忆与情感信任。
这份无形的情感资产,才是娃哈哈穿越四十年风雨的护城河。而这场内斗,正将这份信任无情地透支,将品牌形象从“可靠的童年回忆”迅速转向为“混乱的家族闹剧”。
另外,这次争夺可能对内部运营体系造成的影响,也正危及娃哈哈的运营基础。娃哈哈是一个庞大的快消帝国,其运转依赖于一个精密而敏感的系统:从生产、物流、到数以万计的经销商。如今的家族内斗,正悄然冲击这个系统的一些关键节点。所以,它不是表面的继承风波那么简单,而是直接威胁到娃哈哈赖以生存的组织肌理。
大股东的这次出手,或许不仅是解决当下的矛盾,更可能会影响一个被长期忽略,但却至关重要的问题,那就是大股东与宗庆后时代所形成的战略默契,正面临瓦解。
在宗庆后执掌娃哈哈时,公众普遍认为,宗庆后就是这家企业的化身,是这家企业的图腾,这是一种基于情感、基于历史、基于宗庆后个人影响力的深层认知绑定。作为大股东的国资,鲜少露面,几乎是隐身一般存在。
但这与法律事实上的股权结构并不吻合。娃哈哈集团的第一大股东,是杭州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,持股比例为46%,宗庆后家族持股29.4%,娃哈哈职工持股会则持有剩余24.6%股权。
某种程度上,作为大股东的上城区国资委,也正是基于宗的个人贡献、带领企业所取得的成绩,与其形成了高度的战略默契,作为大股东,对其充分信任,不过问、不干预、不插手、默默守护。
这也形成了宗庆后时代,极为特殊的哇哈哈治理模式。在这个治理体系下,娃哈哈等于宗庆后、宗庆后等于娃哈哈。而他也用四十年的时间证明,他的个人信用,就是国资股东资产保值增值的最大、最可靠保障。
在这样一位“定海神针”式的人物面前,作为大股东的国资,选择不干预,也是最智慧、最高效的选择。
宗庆后的离世,意味着过去那种基于个人权威的、心照不宣的战略默契,到了面临考验的时刻。而从当下所面临的种种现实来看,这种战略默契的基础已然不再牢靠,国资股东的角色必须发生根本性转变。
当企业肌体健康、高速发展时,它可以是一位沉默的财务投资者,享受分红,静待花开。但当企业面临被内斗冲击、品牌价值受损的现实危险时,它如果继续沉默,就不再是智慧,而是失职。
对大股东来说,保护娃哈哈这块金字招牌,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选择题,而是一道法律与道义的必答题。娃哈哈的背后,不仅是价值数百亿的国有资产,更是数万名员工的生计与家庭,也是杭州过往发展中的一张名片。
任何一个负责任的资产管理者,都绝无可能坐视这笔巨大的公共财富,被家族内斗的漩涡所冲击和影响。所以,杭州专班的介入,或许本质上并非为了处理二股东的家事,而是在公司治理框架内,为避免公司受影响而行使的合法权利。
但其作为具有实质影响力的决策者,某种程度上也会对这场豪门争夺战施加影响,使其不致于进一步滑向失控的边缘。